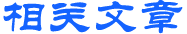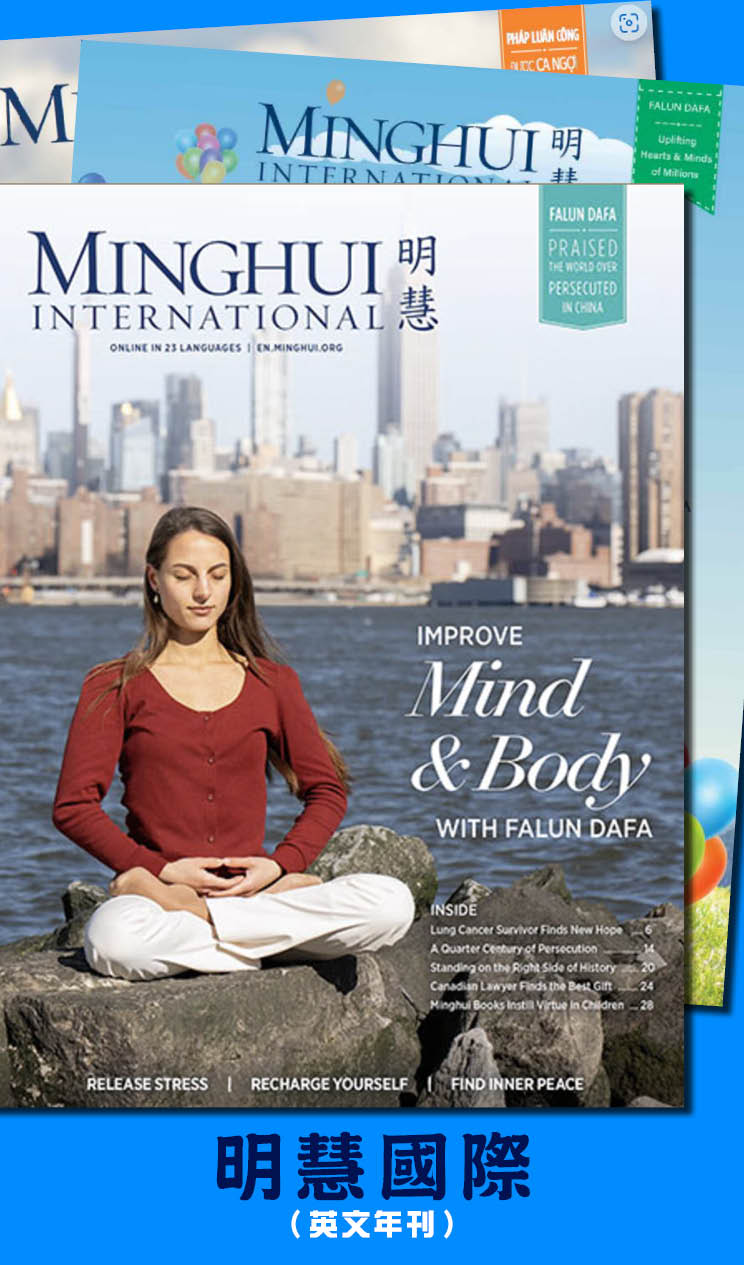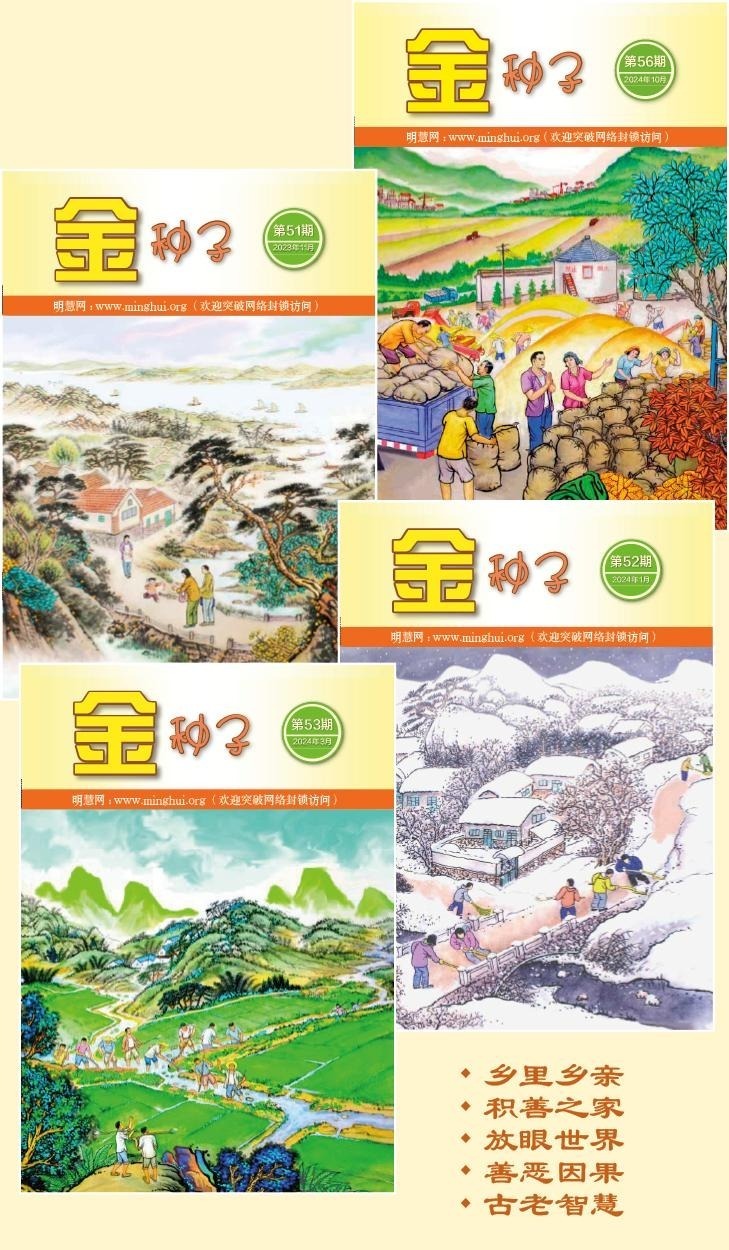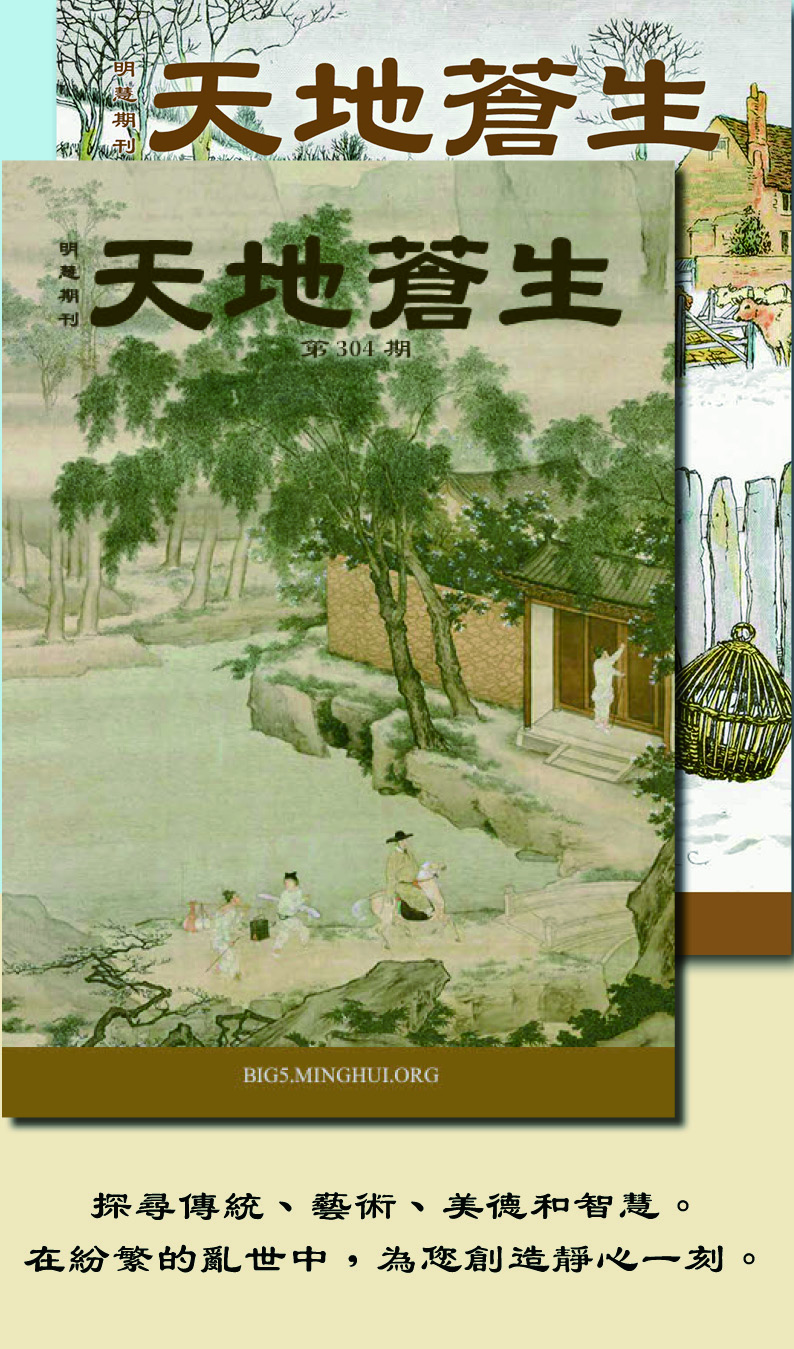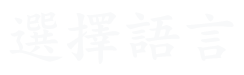突然,一个年轻警察向我愤怒的喊: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?!我猛然被惊醒,意识到这些警察被中共用谎言毒害着,用利益驱使着,而我却没有用修炼人的善良去理解他们、救度他们。想到这儿,我把说话的语调放缓,紧绷的氛围也轻松了许多。我说:我是希望你们平安。说到这儿,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。两个警察对视了一下,不审了。但最后我仍被非法拘留十五天。
非法拘留结束后,我回到家中,觉的还有好多话没有和这些警察说清,真是有些遗憾。还要去派出所讲清真相吗?我问自己。毕竟多年打压迫害的原因,在我的眼里,派出所那个地方就好象是虎穴,要是以往,我真的不想去。这些年来,派出所的警察为完成所谓的“清零”任务,多次想找到我,都被我回避了,所以他们这次处心积虑的跟踪绑架。但我又觉的应该去,理由很简单:我是大法弟子,他们是众生!而且现在疫情很严重,他们更需要健康与平安!于是,我决定到派出所找教导员要东西,能借助这个机缘和他们再讲讲真相。
教导员很忙,有时开会,有时不在,我就和办案的警察、大厅里的警察讲真相。我说文革结束的时候,那些积极与整人的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,只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了事。我们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,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,现在办案终身制,这样你们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。疫情这么严重,你们每天还这么辛苦,要保重好身体啊……有的警察点头;有的警察说是;还有一个警察脸上抽搐了一下,猛然转过身,似乎是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我一共去了四次派出所,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几乎都听过我讲的真相了,尤其是这些年轻警察都“大姐、大姐”的叫着我,个个都象是我的亲弟弟。
二零二四年八月,我在早市发真相期刊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,被抓到某派出所,我和这个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,他们也不想处理这个事,最后又把我推给了户籍所在的派出所负责。我刚被带到户籍所在派出所,一个警察见到我,面带难过的神情说:大姐,你咋又被抓了?教导员见到我,也说:你又来了,你母亲自己在家可咋办呢?
因为我母亲年纪太大,沟通起来困难,他们打电话通知了我的一个亲戚。亲戚急匆匆的赶来后,教导员独自悄悄的对她说:你赶快去她家,收拾下东西。我们按“程序”,一会儿得去她家查查。亲戚说:那也来不及啊,干脆你们上我家查吧。教导员同意了。
我当时并不知情。由于所谓的“执法过程”需要全程录像,我被戴上手铐,随后又被三个警察带上车。我发现这几个警察都换上了便装,他们个个都是身高体壮的,穿着的背心却有点儿紧,看起来不太合体。我感到有点儿奇怪。不一会儿,却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亲戚家所在的小区。为了不引起小区居民的注意,下车后警察用衣服遮挡住我被铐着的双手。
到了亲戚家,三个警察又换上了警服,在执法仪的镜头下开始“执法”:他们指着一个衣柜问我亲戚:这是你俩的衣服吗?亲戚说:是的。然后他们大致翻了翻,又看看书柜和其它地方,一会儿就作罢。大家都心知肚明,一切都是做样子。
最初,派出所里只有一个新来的年轻刑警对我很凶,我没有被他带动,我对他说:其实你很善良的。他反问到:我善良吗?我说:你很善良啊!之后,他就对我很客气了。在车上,他不时关切的问我手铐紧不紧,坐的姿势得不得劲。
整个过程,我的感受就是——我变,警察也变了。这些可贵的生命值得被救度!